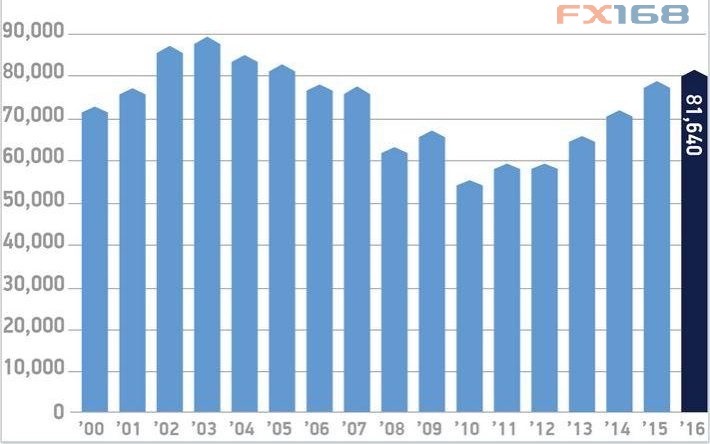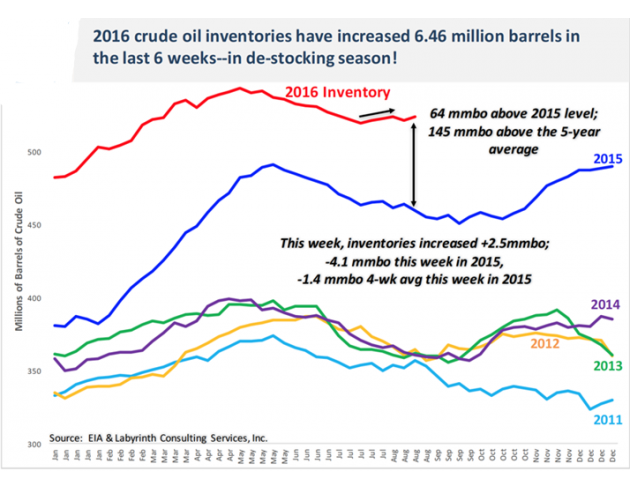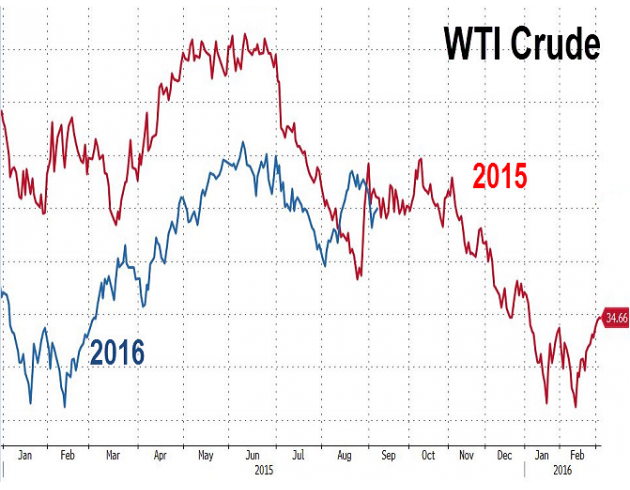漏船载酒泛中流——金融危机8周年回望
本刊记者 陆晓明/文
八年前,当美国次贷危机演进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全球经济似乎又面临一场类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
但事态的发展让人庆幸,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的经济衰退都没超过五个季度,其间美国GDP累计衰退3.1%;欧盟衰退4.4%;日本衰退6.5%;拉美仅下滑1.3%。而“大萧条”那次,美国经济连续衰退四年,GDP累计萎缩26.3%;西欧12国衰退三年,累计萎缩9.5%;日本经济萎缩7.3%;拉美主要8国也衰退三年,累计萎缩14.7%。可见,这次衰退无论是时长还是深度都远不及“大萧条”。
尽管这次衰退的深度低于预期,复苏早于预期,但随后的复苏进程却相当难看。欧元区经济复苏六年才回到危机前水平,比“大萧条”那次多花了三年;复苏第七年时GDP总量仅比危机前水平高出2.1%,还不到上次22.4%的零头。这次日本经济总量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花了四年,比上次多花两年;复苏第七年时GDP总量仅比危机前高出1.4%,而上次第七年已超出危机前水平28.8%。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这次复苏相对较快,复苏两年经济总量就回到危机前水平,比上次少花一年;但复苏势头却不及上次强劲,复苏第七年时GDP总量大约比危机前高出12.7%,而“大萧条”那次复苏第七年GDP总量已超出危机前19.8%。
这次复苏极其缓慢乏力,显然与复苏方式有关。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产泡沫破裂,大批金融机构因资产缩水而资不抵债从而破产倒闭。危机中,金融机构“现金为王”的本能反应更使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融资的功能急剧弱化,经济失血由此进入衰退。按照当今的主流理论,这时央行应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维护金融稳定,财政政策也该逆市刺激,直接支持实体经济。
的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央行迅速联手降息,七家主要央行短短三个月内就降息近两个百分点,降到1%以下;而“大萧条”那次,花了20个月才降了两个百分点到3.5%。尤其是,这次全球央行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而上次受制于当时的金本位,七家主要央行的货币发行在危机第一年基本按兵未动,随后三年甚至下降了11%。
财政政策方面,上次“大萧条”时,政府墨守“量入为出”的成规,危机爆发后第一年,24个国家的总体财政收支与之前几年一样基本平衡,之后三年赤字占GDP比例才缓缓扩大到3%。现在的政府很干脆,危机爆发后一年,24个国家的综合赤字就超过GDP的5%,主要发达国家超过7%。
“大萧条”时政府的不作为被认为加剧了衰退,而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推出的超级宽松货币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显然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但是否可认为,上次“大萧条”时经济按自身运行方式市场出清比较彻底,泡沫尽破,为后来强劲的复苏提供了“铁底”的坚实基础?而这次全球协同救市虽然遏制了衰退的深度,但也维持了泡沫,使之后的复苏踩着泡沫一步一滑,至今步履为艰?
基于这样的担忧,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之际,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之时,笔者曾撰文指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能量尚未完全释放,只是被全球协同救市措施所暂时压住,剩余的破坏能量若又一次集中爆发将会造成‘二次探底’,而其逐渐释放则将形成主要经济体经济的长期低迷,类似于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时隔六年,现在看来,还真有些不幸言中。
由于这次复苏持续乏力,本来短期的逆周期刺激政策至今无法退出,似乎已成常态,而且几乎已用到极致,主要央行的利率已几乎降到零,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债已是负利率,发达国家的国债过去八年的增量已超过之前数百年累计的总额。但如此超级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疲弱经济的扶持效力却日趋递减,颇呈“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尴尬,甚至“漏船载酒泛中流”的险象。
现在的问题是,按以往全球经济每8-10年经历一次低谷的周期性“规律”,下一场衰退或许已为期不远。届时,各国政府和央行是否还有充足的弹药应对一场新的危机?